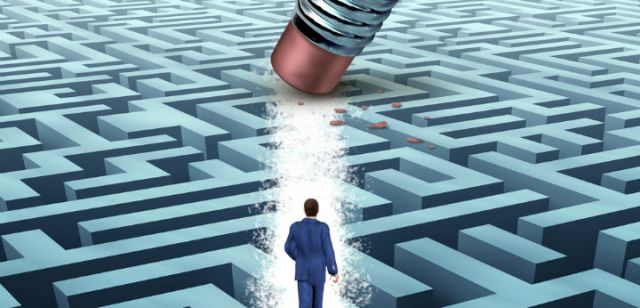撲面而來的“大變局”敘事,一時間讓大宏觀、大歷史成爲金融市場上的顯學。最近,各路聲音對貨幣變遷的回眸、對美元體系的撻伐,且不說深刻與否,至少足夠密集。使人不得不承認:金融市场确实是敘事的制造机。才半年以前,有關“美國例外”的種種迷思還在全球瀰漫,至今一看,已恍如隔世。
不過,敘事的動聽和傳播性是一回事,合理性則是另一回事。後者考驗的是細節勾稽的嚴密,也即所謂“框架”,這最能體現一個人的“宏觀功底”。我們往往發現,許多盛行的結論在框架上並不嚴密,很容易落入以偏概全、過度聯繫、滑坡謬誤等等陷阱,因而不難理解,不少嚴肅的宏觀研究者對宏大敘事,反而抱着直覺性的警惕。但如今,事情已經起了變化,我們越來越感到“(把數據和邏輯)拆的越細越好”的技藝,並不是宏觀唯一的維度,甚至有時候也會一葉障目。既然宏觀多少還算是一門“屠龍術”,那麼適度的想象力仍然是必要的——“打破邊界,想點大事”。
所以,我們不妨來認真地聊聊:“美元霸權”的退潮將如何發生,又將影響我們熟知的世界?
是誰創造了“美國例外”和“美元霸權”的神話?沒必要羞於承認,是全球市場幾乎每一位金融從業者。無論你是否直接參與了美股的長期牛市,只要你接受了它的敘事,便已身在其中。其中不僅有對美國經濟和市場的直接認知,更有我們非常熟悉的一些“常識”,比如:
·宏觀政策“各司其職”: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相互獨立,又服務於逆週期的目標;
·宏觀經濟向“樣板”收斂:經濟增長的結構會向消費和服務驅動轉型,而经济增速和利率水平会向某个中长期中枢收斂;
·資產價格的“均值迴歸”:匯率會向利率平價收斂、期貨價格會向現貨價格收斂、風險溢價和收益率曲線會向歷史均值收斂……
這些“常識”的表象可謂大相徑庭,爲什麼說他們都和美元霸權相關呢?需要看到,它們都基於同一個基準假設,即“低波動率”:政策的波動率應該下降(來自明確的承諾和約束)、經濟增速的波動率應該下降(消費比投資要更少“脈衝”)、資產的波動率應該下降(總有流動性的提供者出現)……然而,波動率實際上並不具有“自動穩定”屬性,反而是自我強化的:低波動時流動性充裕,而流動性充裕又創造了低波動,反之亦然。類似的,政策和經濟增長也遠非“自動穩定”——毋寧說,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,二者陷入惡性循環屢見不鮮。那麼,當我們將“波動率的自我穩定”当作一种常識,實際上就是默認接受了一種“外來的權力”將提供流動性兜底,而“美元霸權”的貨幣權力,就是這一系統性權力的關鍵側面。
需要看到,美元作爲一種貨幣霸權相當特殊:它是人類在告別金本位、擁抱信用貨幣後的第一個、也是唯一一個貨幣霸權。也因而,“美元霸權”的運作既有美元作爲一種主權貨幣的特殊性,也有信用貨幣機制下的普遍性。派生貨幣的“信用”和美元本身的“信譽”,這兩個概念雖然有相當的差異,但我們發現又很難互相剝離。“低波動率”邏輯最終實現閉環,正依靠這一權力體系的“信譽”所創造的流動性和宏觀穩定。
但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:這一信譽本身面臨巨大的挑戰。
長久維持的信譽往往是“非人格化”的,它內嵌在制度裏,成爲了“合法性”。在原初的時候,制度往往建立於強制甚至暴力之上,但又使自己在後續的大部分時候免於使用強制或暴力,這一過程中的關鍵,是對被統治者形成“內化威懾”的規訓:我們默契地認爲,這些制度在運行的結果上踐行了公共利益,而挑戰它們,將使包括挑戰者在內的所有人受損。美元霸權也是如此:儘管“石油美元”以及更早前的一系列貨幣安排確實具有一定的強制色彩,但直到如今,其霸權的廣度已然超越了這些安排,其邊界,根本上取決於信譽的邊界。
然而,信譽的邊界只是一個“想象”的概念,在實際中,它往往是模糊的。對制度的批評和否定時刻存在,有些甚至相當深刻,但這不代表制度馬上就面臨不安全。在大多數時候,制度的好處直接、明確、集中,壞處卻間接、模糊、分散。比如一直以來,都有很多聲音批判“美元潮汐”對各國的反覆收割,誠然如此,但同樣不可否認,許多經濟體都從這個貨幣霸權中獲得了好處:信用溢價的下降、貿易的擴張、資本的流動、工業化的進程等等。美元是一種重要的基礎設施,對全球化、分工和全球金融市場穩定起着關鍵作用——霸權總需要提供這些公共品,而這也使得集體意識傾向於接受“內化威懾”的邏輯結果,甚至拒絕“戒斷”的痛苦。而一個潛在的推論是:其信譽的消失不會是一個線性的過程,而往往需要一場“擠兌”。
因而,讓“不信任”覺醒成爲主流共識的“催化劑”很重要:就像那個寓言裏的老爺爺,當被別人問到睡覺時該把鬍子放在被子裏還是被子外,他就睡不着了。而这个催化劑会来自何方呢?
我們不妨猜想:
一方面是來自“主權貨幣”層面,它根植於制度的破壞。比如,政治是要“裝”的,要遵循儀式、體現程序的合法性,比如紀要、備忘錄和紅頭文件雖然古板,但終究不能被社交媒體和羣聊所取代。歸根到底,美元霸權很大程度上來自對美國政治制度作爲一種自稱“最不壞的制度”的底層信任,如果這一套制度本身被“祛魅”,或更直接點,作爲美元流動性最終提供者的美聯儲被捲入白宮的破壞性議程之中,進而無法在“明面上”保持於政治利益之外,那麼美元及其金融體系也自然難以保持信任。
而另一方面則來自“信用貨幣”體系層面。在此,我們又能發現兩個相互交織的問題:一是財政和債務的可持續性,二是貨幣政策的有效性。我們上文提到,“常識”認爲財政和貨幣的相互獨立,最集中表現的就是,經典的宏觀分析中,我們有一張“政府的(資產負債)表”,也有一張“央行的(資產負債)表”。爲什麼二者不能合併?基礎貨幣不能成爲政府的負債呢?學理上既有反對者,也有支持者。不過說到底,這兩張表都只是金融市場的“心理賬戶”,在這裏,“市場審美”構成了一道防火牆:只要多數市場參與者把貨幣決策作爲一個技術問題(而不是政治問題),只要財政和貨幣當局願意表現出“表面上”的負責制、劃定債務衡量的標尺、以及展現出追求平衡的努力,那麼市場就能夠接受“可持續”的敘事,進而繼續接受央行的流動性,併爲財政的融資買單;而反之,一旦這種“表面功夫”坍塌,央行的“無限子彈”甚至在幾個瞬間可以等同於“非法”,比如2022年英國的財政信任驟然演化成貨幣危機,展現了一場經典的“突然停止”。類似的事情其實在新興市場經常發生,但近些年,火勢開始向發達市場蔓延,這顯然不是一個好的徵兆。
不過,最近一系列的動盪,已然指向了美元霸權的危機嗎?至少目前,答案是否定的。幣值是貨幣危機的最直接表徵,一方面是匯率這個外部幣值,另一方面則是通脹這個內部幣值。歷史的最具聲名的案例便是魏瑪德國——對外劇烈地貶值,對內劇烈的通脹。在此背後,是外債的巨大壓力、不可逆轉的資本外流不可逆轉,失去主導權的央行。至少目前,美元指數從高點10%的下跌,尚不足以表徵一場禮崩樂壞,而美國通脹的絕對水平也不支持這一場景。不過,潛在的風險點隱隱可見:通脹在疫情之後打破了長期穩態,進而有潛在的擴散性(而不是收斂)。那麼,理論上“一次性”的關稅是否又會成爲一個催化劑?我們已經看到一些早期的證據:消費者調查的通脹預期在擴散,通脹的“寬度”也在提升。但目前仍難以下確切的判斷,還有待繼續觀察。
我理解,很多人對宏觀研究印象往往是:洋洋灑灑說了一堆,但是落到最後,都是“不確定”、“再看看”,這很沒意思。所以,不妨我們在這裏大膽地更進一步,嘗試探討:如果美元霸權果真退潮,我們將面臨一個怎樣的世界?
很多人都將這視爲其競爭者的機會,此話不假。但也需要意識到,美元霸權和信用貨幣體系的一體兩面屬性,美元這一側的崩潰,不會伴隨着信用貨幣那一側的完好無損。在“美麗新世界”之前,一段風雨如晦的動盪期無疑不可避免——在一個缺乏信任的世界裏,首先到來的將是更頻繁的流動性問題和波動率的中樞上升,這意味着在“進攻”或“建構”之前,最關鍵的是“防禦”:對於資本市場,要做好“均值迴歸”和“套利交易”失效的準備,歷史的錨定或許無法提供確定性,極端的衝擊可能進一步極端;而在宏觀上,必須考慮流動性衝擊甚至“突然停止”的宏觀後果,經濟可能隨時面臨“(有效)貨幣供應不足”的環境。
而既然挑戰是屬於每一方的,那麼下一個問題自然是:如果美元最終走下霸權,那麼美元會更強還更弱?
不必懷疑,第一直覺的答案是弱。我們已經看到很多資金逃向非美、低息甚至零息的安全資產,美元的對沖比例成爲最近最熱門討論話題,歐元、日元和黃金已經相當擁擠……這些頭寸有短期的合理性,但拉長來看,它們或許只是對“美元退潮”的短期情緒化的反映。只要匯率還在相對的自由浮動的領域,這個問題便可以轉化爲:美國對非美的相對優勢是增大還是減少?答案並不確切。一方面,這是一場脆弱性的較量,歷史經驗顯示,在秩序重構的進程中,邊緣往往塌陷得比核心更快,累積的脆弱性將更快爆發;而另一方面,這會變成一場“逐底競爭”的遊戲:就像世界在20世紀30年代面臨“不得不放棄金本位”的考驗時,誰把歷史包袱丟得越快,就越早感受到貶值的好處;而誰堅持着歷史包袱,自然有短期更強的信譽,但也必須承受貨幣高估的代價——對一種古老的安全的渴望,可能反而會創造不安全。無論如何,資本管制這一選項的誘惑力會越來越大,而被學理的“應然性”包裹很重的自由浮動,也是一種危機時被迫的選擇。
那麼,另一種古老的安全信仰,黃金是否可能很有機遇呢?這是一個包裹了太多迷思的物品。很多人說,黃金的機會不是顯而易見嗎?它是一種古老的信仰、天然的貨幣、諾亞方舟……無法反駁,確實如此。但就我自己而言,無法輕易地預言黃金的長期圖景,就像我無法站在2009年去預言加密貨幣的未來:它的巨大成功離不開一連串的時運,甚至需要它作爲一個挑戰者和美元體系的深度融合(通過穩定幣的底層儲備),這並非僅憑信仰可以預見的。人們關於黃金的共識會有限度嗎?我相信是有的。黃金或許能像一艘小舟,在信用貨幣的潰退中留住一部分無處可去的價值,這可能足以使它的價格繼續走向深空。但對於宏觀世界來說,“金本位”本身是沒有意義的:縱使這種天然通縮的貨幣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解決信任的問題、貯存的問題、甚至可交易的問題,但最終無法匹配這個已經見過金融加速器的年代——它解決不了發展的問題。而到最終,或許也解決不了信任的問題。只要你相信貨幣仍應該有主權,那麼它的定价便应该体现这个主权者创造的价值、帶來的進步、治理的能力,而不是它囤積的金屬。這也意味着,擊潰“美元霸權”最終需要“建構”和“重塑信任”:我們有更具實際的、負責制的方法,來兼顧逆週期的必要、經濟效率和制度信任的多方平衡。
而另一個迷思是,商品是否可能很有機會?不少海外的“宏觀大師”認爲,出於安全考慮,不少國家都會囤積資源,所以應該做多商品,甚至前些年有主張以商品作爲“貨幣本位”者。這一邏輯僅具有狹窄的正確性。且不說供給端的諸多變數(比如原油),僅僅考慮需求端,這般理解也似乎過於簡單:大量的囤積行爲必然面臨經濟性的約束,而庫存作爲投資的一種形式,也必然會形成某種意義上的“擠出”,進而反作用到需求,一个只有安全需求而擠出了经济需求的世界,恐怕不會對商品太過於友好。而更進一步來說,假設你作爲一個國家的領袖,打算在當前環境下爲“最壞的情況”做些準備,那麼最基礎的假設一定是一場持久戰——而儲備,無論它能維持30天、50天、100天,都只能帶來虛假的安全感,絕不是可以無限且無度的。人類的戰爭史已經表明:相比起儲備的多寡,最重要的對資源和航路的直接控制,而這些歸根到底,都只能建立於武力和冒險之上,這一點對大國尤爲成立。
不過無論如何,貿易還會存在,就像日月星辰會一直存在下去,只是政治的色彩會更明顯。這可能只是迴歸歷史的引力:在人類漫長的過去,貿易和政治本就密不可分,一個輪子本來就要被髮明許多遍。只是現代以來,我們更習慣用全球化、自由貿易、經濟效率等等視角來宏觀地理解貿易,而略去了具體的貿易談判中的政治性,以及自由貿易本身内嵌的政治意图。所以最終,我們將要討論的一個“政治顯性化”的經濟世界,這樣一個世界中,機會在哪裏呢?不妨如此推論:
“騎牆派”的國家將會有機會,它們將成爲貿易中轉的節點,甚至可能發揮“小國牽動大國”的角色;
貿易商和冒險家將會有機會,對技術和新東西的嚮往、以及對基本品的渴望,永遠是人類的剛需,而打破貿易的藩籬將越來越具有技巧性、並且有利可圖;
“東印度公司”將會有機會,跨國公司將越來越直接地承擔了大國的利益和力量投射,它們甚至可能擁有一定意義上的領土和“治權”,不僅在於真實世界,也在數字的邊疆;
社交媒體將會有機會,內容和流量最容易跨過被封鎖的邊界,也最容易塑造一種敘事,它們將成爲權力的戰場。
……
無疑,這個世界看起來古老且眼熟,又因新的科學和治理技術而陌生。人類歷史上有很多年沒什麼大事,它們的和平和繁榮只爲當世之人知曉,構成了史書上不爲人察覺的空白;而也有短短一瞬,一切都發生了,這一瞬變得很長、很厚。經過了這一瞬人們便發覺,在空白期的常識和信仰,實際上輕如鴻毛——歷史不曾有過終結,也不曾提供永恆的樣板,它只是處於永恆的動盪中。我想,我們已經越來越接近這樣一瞬間的開始。而在這樣的環境裏,我想,第一應該做的是“珍惜你的信任”,基於歷史經驗或者某個機構的能動性,終歸是不可靠的;第二是依靠“第一性”的歷史邏輯,不要過度依賴短期的現象和情緒和做出判斷;第三是打開想象:既敢於想象一些艱難的、不可思議的情況;也敢於想象一些樂觀的未來,畢竟,信念永遠是行動、改變世界的第一動力。
來源:青野有枯榮,原文標題:《翻越常識之牆:想象“後美元霸權”的金融秩序》
風險提示及免責條款 市場有風險,投資需謹慎。本文不構成個人投資建議,也未考慮到個別用戶特殊的投資目標、財務狀況或需要。用戶應考慮本文中的任何意見、觀點或結論是否符合其特定狀況。據此投資,責任自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