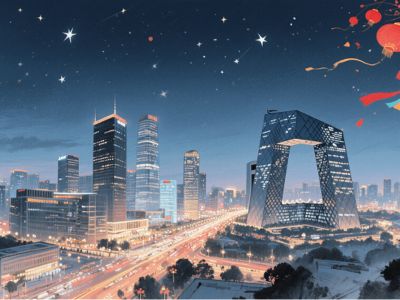扑面而来的“大变局”叙事,一时间让大宏观、大历史成为金融市场上的显学。最近,各路声音对货币变迁的回眸、对美元体系的挞伐,且不说深刻与否,至少足够密集。使人不得不承认:金融市场确实是叙事的制造机。才半年以前,有关“美国例外”的种种迷思还在全球弥漫,至今一看,已恍如隔世。
不过,叙事的动听和传播性是一回事,合理性则是另一回事。后者考验的是细节勾稽的严密,也即所谓“框架”,这最能体现一个人的“宏观功底”。我们往往发现,许多盛行的结论在框架上并不严密,很容易落入以偏概全、过度联系、滑坡谬误等等陷阱,因而不难理解,不少严肃的宏观研究者对宏大叙事,反而抱着直觉性的警惕。但如今,事情已经起了变化,我们越来越感到“(把数据和逻辑)拆的越细越好”的技艺,并不是宏观唯一的维度,甚至有时候也会一叶障目。既然宏观多少还算是一门“屠龙术”,那么适度的想象力仍然是必要的——“打破边界,想点大事”。
所以,我们不妨来认真地聊聊:“美元霸权”的退潮将如何发生,又将影响我们熟知的世界?
是谁创造了“美国例外”和“美元霸权”的神话?没必要羞于承认,是全球市场几乎每一位金融从业者。无论你是否直接参与了美股的长期牛市,只要你接受了它的叙事,便已身在其中。其中不仅有对美国经济和市场的直接认知,更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“常识”,比如:
·宏观政策“各司其职”: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互独立,又服务于逆周期的目标;
·宏观经济向“样板”收敛:经济增长的结构会向消费和服务驱动转型,而经济增速和利率水平会向某个中长期中枢收敛;
·资产价格的“均值回归”:汇率会向利率平价收敛、期货价格会向现货价格收敛、风险溢价和收益率曲线会向历史均值收敛……
这些“常识”的表象可谓大相径庭,为什么说他们都和美元霸权相关呢?需要看到,它们都基于同一个基准假设,即“低波动率”:政策的波动率应该下降(来自明确的承诺和约束)、经济增速的波动率应该下降(消费比投资要更少“脉冲”)、资产的波动率应该下降(总有流动性的提供者出现)……然而,波动率实际上并不具有“自动稳定”属性,反而是自我强化的:低波动时流动性充裕,而流动性充裕又创造了低波动,反之亦然。类似的,政策和经济增长也远非“自动稳定”——毋宁说,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,二者陷入恶性循环屡见不鲜。那么,当我们将“波动率的自我稳定”当作一种常识,实际上就是默认接受了一种“外来的权力”将提供流动性兜底,而“美元霸权”的货币权力,就是这一系统性权力的关键侧面。
需要看到,美元作为一种货币霸权相当特殊:它是人类在告别金本位、拥抱信用货币后的第一个、也是唯一一个货币霸权。也因而,“美元霸权”的运作既有美元作为一种主权货币的特殊性,也有信用货币机制下的普遍性。派生货币的“信用”和美元本身的“信誉”,这两个概念虽然有相当的差异,但我们发现又很难互相剥离。“低波动率”逻辑最终实现闭环,正依靠这一权力体系的“信誉”所创造的流动性和宏观稳定。
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:这一信誉本身面临巨大的挑战。
长久维持的信誉往往是“非人格化”的,它内嵌在制度里,成为了“合法性”。在原初的时候,制度往往建立于强制甚至暴力之上,但又使自己在后续的大部分时候免于使用强制或暴力,这一过程中的关键,是对被统治者形成“内化威慑”的规训:我们默契地认为,这些制度在运行的结果上践行了公共利益,而挑战它们,将使包括挑战者在内的所有人受损。美元霸权也是如此:尽管“石油美元”以及更早前的一系列货币安排确实具有一定的强制色彩,但直到如今,其霸权的广度已然超越了这些安排,其边界,根本上取决于信誉的边界。
然而,信誉的边界只是一个“想象”的概念,在实际中,它往往是模糊的。对制度的批评和否定时刻存在,有些甚至相当深刻,但这不代表制度马上就面临不安全。在大多数时候,制度的好处直接、明确、集中,坏处却间接、模糊、分散。比如一直以来,都有很多声音批判“美元潮汐”对各国的反复收割,诚然如此,但同样不可否认,许多经济体都从这个货币霸权中获得了好处:信用溢价的下降、贸易的扩张、资本的流动、工业化的进程等等。美元是一种重要的基础设施,对全球化、分工和全球金融市场稳定起着关键作用——霸权总需要提供这些公共品,而这也使得集体意识倾向于接受“内化威慑”的逻辑结果,甚至拒绝“戒断”的痛苦。而一个潜在的推论是:其信誉的消失不会是一个线性的过程,而往往需要一场“挤兑”。
因而,让“不信任”觉醒成为主流共识的“催化剂”很重要:就像那个寓言里的老爷爷,当被别人问到睡觉时该把胡子放在被子里还是被子外,他就睡不着了。而这个催化剂会来自何方呢?
我们不妨猜想:
一方面是来自“主权货币”层面,它根植于制度的破坏。比如,政治是要“装”的,要遵循仪式、体现程序的合法性,比如纪要、备忘录和红头文件虽然古板,但终究不能被社交媒体和群聊所取代。归根到底,美元霸权很大程度上来自对美国政治制度作为一种自称“最不坏的制度”的底层信任,如果这一套制度本身被“祛魅”,或更直接点,作为美元流动性最终提供者的美联储被卷入白宫的破坏性议程之中,进而无法在“明面上”保持于政治利益之外,那么美元及其金融体系也自然难以保持信任。
而另一方面则来自“信用货币”体系层面。在此,我们又能发现两个相互交织的问题:一是财政和债务的可持续性,二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。我们上文提到,“常识”认为财政和货币的相互独立,最集中表现的就是,经典的宏观分析中,我们有一张“政府的(资产负债)表”,也有一张“央行的(资产负债)表”。为什么二者不能合并?基础货币不能成为政府的负债呢?学理上既有反对者,也有支持者。不过说到底,这两张表都只是金融市场的“心理账户”,在这里,“市场审美”构成了一道防火墙:只要多数市场参与者把货币决策作为一个技术问题(而不是政治问题),只要财政和货币当局愿意表现出“表面上”的负责制、划定债务衡量的标尺、以及展现出追求平衡的努力,那么市场就能够接受“可持续”的叙事,进而继续接受央行的流动性,并为财政的融资买单;而反之,一旦这种“表面功夫”坍塌,央行的“无限子弹”甚至在几个瞬间可以等同于“非法”,比如2022年英国的财政信任骤然演化成货币危机,展现了一场经典的“突然停止”。类似的事情其实在新兴市场经常发生,但近些年,火势开始向发达市场蔓延,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。
不过,最近一系列的动荡,已然指向了美元霸权的危机吗?至少目前,答案是否定的。币值是货币危机的最直接表征,一方面是汇率这个外部币值,另一方面则是通胀这个内部币值。历史的最具声名的案例便是魏玛德国——对外剧烈地贬值,对内剧烈的通胀。在此背后,是外债的巨大压力、不可逆转的资本外流不可逆转,失去主导权的央行。至少目前,美元指数从高点10%的下跌,尚不足以表征一场礼崩乐坏,而美国通胀的绝对水平也不支持这一场景。不过,潜在的风险点隐隐可见:通胀在疫情之后打破了长期稳态,进而有潜在的扩散性(而不是收敛)。那么,理论上“一次性”的关税是否又会成为一个催化剂?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早期的证据:消费者调查的通胀预期在扩散,通胀的“宽度”也在提升。但目前仍难以下确切的判断,还有待继续观察。
我理解,很多人对宏观研究印象往往是:洋洋洒洒说了一堆,但是落到最后,都是“不确定”、“再看看”,这很没意思。所以,不妨我们在这里大胆地更进一步,尝试探讨:如果美元霸权果真退潮,我们将面临一个怎样的世界?
很多人都将这视为其竞争者的机会,此话不假。但也需要意识到,美元霸权和信用货币体系的一体两面属性,美元这一侧的崩溃,不会伴随着信用货币那一侧的完好无损。在“美丽新世界”之前,一段风雨如晦的动荡期无疑不可避免——在一个缺乏信任的世界里,首先到来的将是更频繁的流动性问题和波动率的中枢上升,这意味着在“进攻”或“建构”之前,最关键的是“防御”:对于资本市场,要做好“均值回归”和“套利交易”失效的准备,历史的锚定或许无法提供确定性,极端的冲击可能进一步极端;而在宏观上,必须考虑流动性冲击甚至“突然停止”的宏观后果,经济可能随时面临“(有效)货币供应不足”的环境。
而既然挑战是属于每一方的,那么下一个问题自然是:如果美元最终走下霸权,那么美元会更强还更弱?
不必怀疑,第一直觉的答案是弱。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资金逃向非美、低息甚至零息的安全资产,美元的对冲比例成为最近最热门讨论话题,欧元、日元和黄金已经相当拥挤……这些头寸有短期的合理性,但拉长来看,它们或许只是对“美元退潮”的短期情绪化的反映。只要汇率还在相对的自由浮动的领域,这个问题便可以转化为:美国对非美的相对优势是增大还是减少?答案并不确切。一方面,这是一场脆弱性的较量,历史经验显示,在秩序重构的进程中,边缘往往塌陷得比核心更快,累积的脆弱性将更快爆发;而另一方面,这会变成一场“逐底竞争”的游戏:就像世界在20世纪30年代面临“不得不放弃金本位”的考验时,谁把历史包袱丢得越快,就越早感受到贬值的好处;而谁坚持着历史包袱,自然有短期更强的信誉,但也必须承受货币高估的代价——对一种古老的安全的渴望,可能反而会创造不安全。无论如何,资本管制这一选项的诱惑力会越来越大,而被学理的“应然性”包裹很重的自由浮动,也是一种危机时被迫的选择。
那么,另一种古老的安全信仰,黄金是否可能很有机遇呢?这是一个包裹了太多迷思的物品。很多人说,黄金的机会不是显而易见吗?它是一种古老的信仰、天然的货币、诺亚方舟……无法反驳,确实如此。但就我自己而言,无法轻易地预言黄金的长期图景,就像我无法站在2009年去预言加密货币的未来:它的巨大成功离不开一连串的时运,甚至需要它作为一个挑战者和美元体系的深度融合(通过稳定币的底层储备),这并非仅凭信仰可以预见的。人们关于黄金的共识会有限度吗?我相信是有的。黄金或许能像一艘小舟,在信用货币的溃退中留住一部分无处可去的价值,这可能足以使它的价格继续走向深空。但对于宏观世界来说,“金本位”本身是没有意义的:纵使这种天然通缩的货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信任的问题、贮存的问题、甚至可交易的问题,但最终无法匹配这个已经见过金融加速器的年代——它解决不了发展的问题。而到最终,或许也解决不了信任的问题。只要你相信货币仍应该有主权,那么它的定价便应该体现这个主权者创造的价值、带来的进步、治理的能力,而不是它囤积的金属。这也意味着,击溃“美元霸权”最终需要“建构”和“重塑信任”:我们有更具实际的、负责制的方法,来兼顾逆周期的必要、经济效率和制度信任的多方平衡。
而另一个迷思是,商品是否可能很有机会?不少海外的“宏观大师”认为,出于安全考虑,不少国家都会囤积资源,所以应该做多商品,甚至前些年有主张以商品作为“货币本位”者。这一逻辑仅具有狭窄的正确性。且不说供给端的诸多变数(比如原油),仅仅考虑需求端,这般理解也似乎过于简单:大量的囤积行为必然面临经济性的约束,而库存作为投资的一种形式,也必然会形成某种意义上的“挤出”,进而反作用到需求,一个只有安全需求而挤出了经济需求的世界,恐怕不会对商品太过于友好。而更进一步来说,假设你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,打算在当前环境下为“最坏的情况”做些准备,那么最基础的假设一定是一场持久战——而储备,无论它能维持30天、50天、100天,都只能带来虚假的安全感,绝不是可以无限且无度的。人类的战争史已经表明:相比起储备的多寡,最重要的对资源和航路的直接控制,而这些归根到底,都只能建立于武力和冒险之上,这一点对大国尤为成立。
不过无论如何,贸易还会存在,就像日月星辰会一直存在下去,只是政治的色彩会更明显。这可能只是回归历史的引力:在人类漫长的过去,贸易和政治本就密不可分,一个轮子本来就要被发明许多遍。只是现代以来,我们更习惯用全球化、自由贸易、经济效率等等视角来宏观地理解贸易,而略去了具体的贸易谈判中的政治性,以及自由贸易本身内嵌的政治意图。所以最终,我们将要讨论的一个“政治显性化”的经济世界,这样一个世界中,机会在哪里呢?不妨如此推论:
“骑墙派”的国家将会有机会,它们将成为贸易中转的节点,甚至可能发挥“小国牵动大国”的角色;
贸易商和冒险家将会有机会,对技术和新东西的向往、以及对基本品的渴望,永远是人类的刚需,而打破贸易的藩篱将越来越具有技巧性、并且有利可图;
“东印度公司”将会有机会,跨国公司将越来越直接地承担了大国的利益和力量投射,它们甚至可能拥有一定意义上的领土和“治权”,不仅在于真实世界,也在数字的边疆;
社交媒体将会有机会,内容和流量最容易跨过被封锁的边界,也最容易塑造一种叙事,它们将成为权力的战场。
……
无疑,这个世界看起来古老且眼熟,又因新的科学和治理技术而陌生。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年没什么大事,它们的和平和繁荣只为当世之人知晓,构成了史书上不为人察觉的空白;而也有短短一瞬,一切都发生了,这一瞬变得很长、很厚。经过了这一瞬人们便发觉,在空白期的常识和信仰,实际上轻如鸿毛——历史不曾有过终结,也不曾提供永恒的样板,它只是处于永恒的动荡中。我想,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这样一瞬间的开始。而在这样的环境里,我想,第一应该做的是“珍惜你的信任”,基于历史经验或者某个机构的能动性,终归是不可靠的;第二是依靠“第一性”的历史逻辑,不要过度依赖短期的现象和情绪和做出判断;第三是打开想象:既敢于想象一些艰难的、不可思议的情况;也敢于想象一些乐观的未来,毕竟,信念永远是行动、改变世界的第一动力。
来源:青野有枯荣,原文标题:《翻越常识之墙:想象“后美元霸权”的金融秩序》
风险提示及免责条款 市场有风险,投资需谨慎。本文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,也未考虑到个别用户特殊的投资目标、财务状况或需要。用户应考虑本文中的任何意见、观点或结论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。据此投资,责任自负。